沙县米酒
常往来于闽江水道上的老人,至今还念念不忘琅口人的好客。琅口镇,史称洛阳镇,曾是闽江上游繁华水路的交通要镇,随处可见货铺、商铺和茶行。“有钱没钱,琅口过年”,说的便是这里的繁华兴盛。琅口人热情好客,就像那句俗语——“琅口街道长又长,红酒鸡蛋炖冰糖”,带着酒香的食物,才是沙县人最盛情的待客佳肴。
沙县人爱米酒,普遍有自酿米酒的习惯,屋角院落,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摆放着一两只酒缸。每有客人来,他们便热情招呼喝酒,喝他们自家酿的红米酒,窖藏多年的,喝一杯就能醉人;婚迎嫁娶、寿诞节气,全族上百人便在厅堂里一起聚餐。这种脱胎于中原传统的民间习俗的家族式饮食风俗,被延续了成百上千年,这一天,族里辈分最大的长者被恭敬地请上首座,开席伊始,第一杯米酒要敬献给他。
沙县人做米酒的传统可以追溯至1000多年前。宋代的沙县酿酒业已初具规模;《周礼》将酒分为“五齐三酒”。“五齐”指的是未经过滤的五种薄酒,其中的“醴齐……一宿而熟,其味稍甜”,分明就是沙县人所称的“酒酿”。《沙县志·物产》记载:夏茂酿造的酒有“长水、短水”之分。长水酿造时间较长,短水则酿造时间较短,与《周礼》中记载的“昔酒”、“清酒”类同。
北宋末年,朱肱曾经撰写《酒经》三卷,对黄酒的加工流程作了详尽的剖析分解,不过沙县酿酒方法,更接近朱肱的另外两篇著述——《武陵桃源酒法》和《冷泉酒法》。
记忆中奶奶是个酿酒能手,有30年的米酒酿造经验。她会选择又长又细的糯米作原料,这种名叫“长粒香”糯米不但出酒量多,还味香醇甜,前一夜她将糯米洗净浸透,翌日,手提笊篱捞起,盛入大饭甑内蒸熟蒸透。蒸熟后,将其倒撒在簸箕或者谷席内摊凉。把摊凉的糯米饭平铺入酒缸底,撒上一层酒粬,再铺一层凉糯饭再一层酒粬,如此反复,直至糯饭酒粬接近缸口,最后注入泉水或井水,以淹没手掌面为宜……酒粬、糯米、井水有严格的比例(2:10:15),对于新手,必须一丝不苟用秤度量,才能保证米酒的出酒率,奶奶不要,她对重量的把握全靠自身对酒粬、糯米与井水习性质地的理解,或多或少,她心中早有自己的尺度标准。米与粬的交流一刻也未停歇,先喃喃细语再喋喋不休最后大打出手……对它们的“淘气”,奶奶有足够的耐心,三天内不管不顾,第四天开始,每日清晨5点,她才准时用一根洁净的木棍搅拌它们几下,两周后她把缸口捆扎结实并加盖,米与粬在发酵中渗透融合,月余即见酒缸中米酒溢满……
经过此一番酿制,沙县的米酒色泽微红,口感香糯,酒香浓郁。虽然没有北方酒的浓烈醇香,却更好入口,且可以驱寒祛风,壮阳滋阴,不仅男人,妇孺都可以分享酒之乐趣。如今,每年新米下来,仍是沙县人酿酒的好时节,九月初九重阳日至翌年谷雨,都是沙县人酿冬酒的黄金时期。“清明茶,谷雨酒”酿一两缸好酒对他们来说是家里的大事,老人们格外重视,他们会慎重地请村里最有文化的“先生”掐出适合造酒的日子——“甲乙日”(农历甲乙开头日,一个月有两天),因为他们都虔诚地信奉祖先流传下来“甲乙做酒就是香,丙丁造酒臭泥浆”的古训。于是“甲乙日”处处可见客家人淘米、洗米、炊米,选酒粬的场景,那一天,百家炊烟袅袅,糯香千里弥漫,“新糯造酒满洋香”是沙县人形容此时造酒现场热闹欢喜的俗语。
新酿的糯米酒,用古老的锡酒壶盛装,后锅水吞温,蒸汽氤氲,诠释着别样的一份热情与温暖。
责编:潘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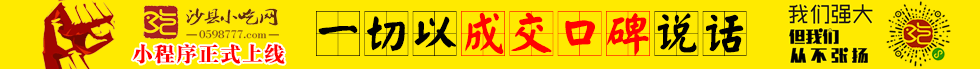
 返回顶部
返回顶部